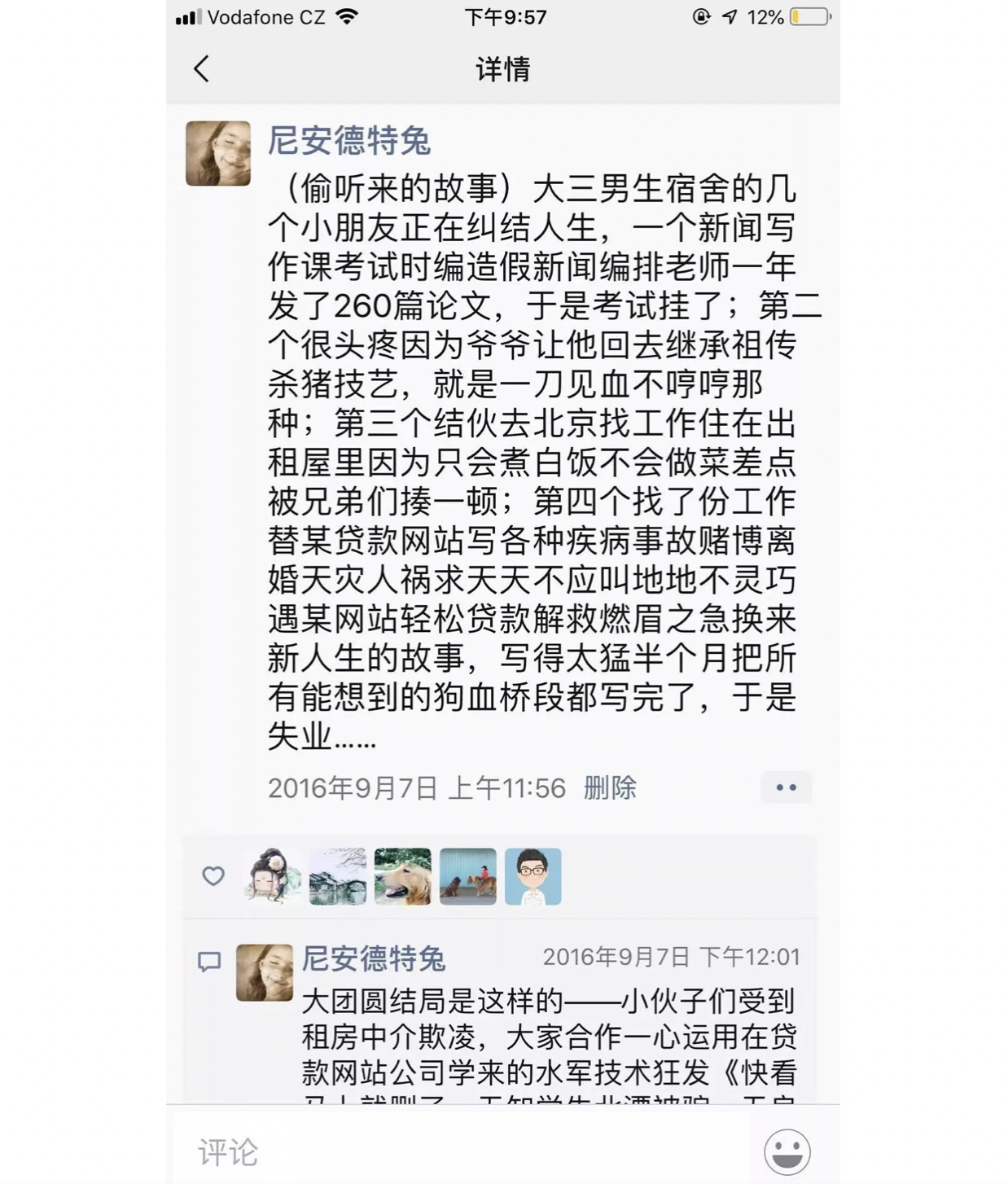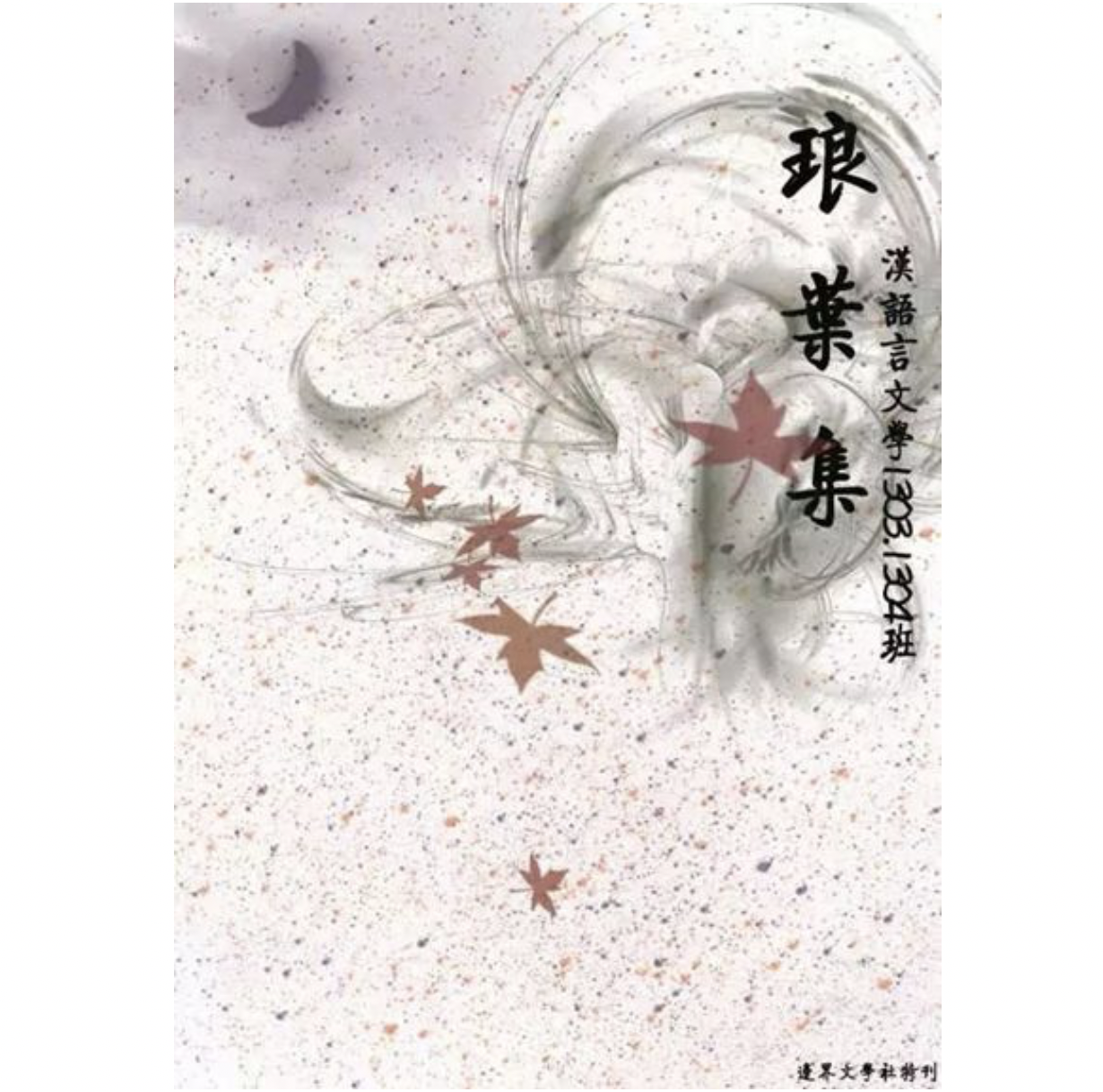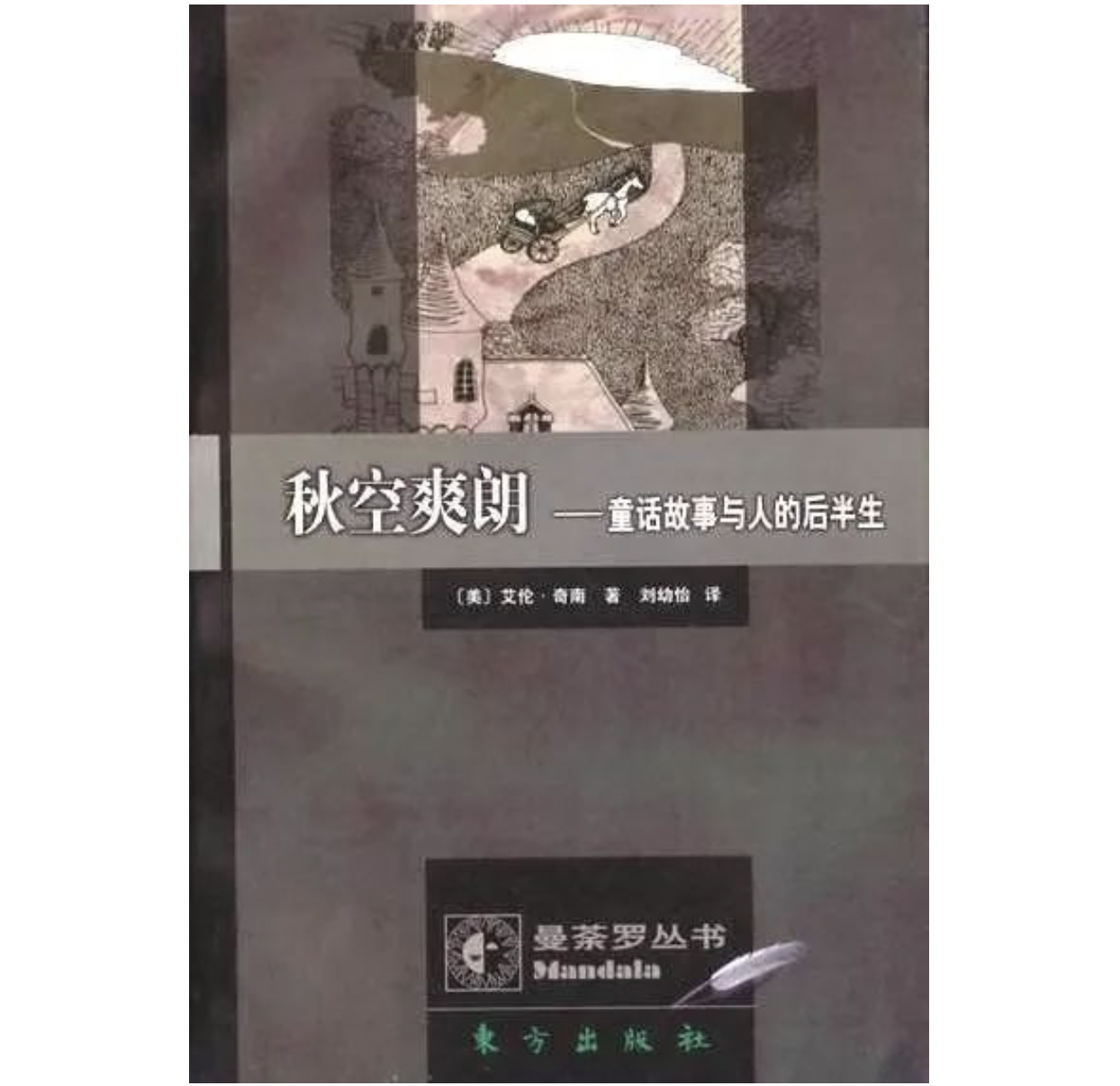| 送交者: 狂心中[♂☆★★★★如狂★★★★☆♂] 于 2019-08-17 4:45 已读 450 次 1 赞 | 狂心中的个人频道 |
昨天,一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刷屏了不少人的朋友圈。刷屏的一个“副产品”,是让不少人对古诗词的用法燃起了考究的兴趣。
在大家印象中,中国古代文学似乎必然对应着传统的社会与时代。学习理解古代诗歌,就是理解古人的哲学与价值观,回到古朴的状态,它与现代社会之间有一层隐形的绝缘体。实际上这一想法可能把古人跟古文,都狭隘化了。
江南大学的古代文学副教授黄晓丹,每天的工作,就是要给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讲古代文学课。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而她讲述每个诗人的方法,也非常不一样,她会给学生一整节课的时间先去校园里散步,然后再回来讨论描写春日的古诗;她工作的第五年,依然跟逃课的学生掰扯“你说得清你把上课的时间拿去看什么书了,我就放你走”;在讲《诗经》时怂恿学生去学校后面的湖里摘荇菜。不喜欢她的同学每天忧心忡忡期末考试到底会考什么,喜欢她的学生则管她叫“兔老师”。
黄晓丹,江南大学古代文学副教授。
在白天给学生上完课后,有些晚上,她还要在只有一盏台灯亮着的单身教师宿舍里,为她同龄的朋友们讲解诗歌,同时也讲解着她们共同的青春记忆与生命焦虑。
2019年,在朋友的建议下,黄晓丹把课程录音整理出来,重新增补了资料注解,完成了《诗人十四个》这样一本小书。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古代文学论著,每一个诗人都以偶然和随意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书籍的装帧正如她想表达的那样——一种融合了惊喜、未知、成形与变形的青春经验。这本结合了古代诗词与现代心理学,还有人生种种走神与惊奇瞬间诞生的感悟的小书,让古诗距离我们如此之近。
6park.com 《诗人十四个》(作者:黄晓丹;版本: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7月)
《书评周刊》的记者宫子正是黄晓丹古代文学课的学生,大学时代的师生情谊让这篇访谈并非那么“一本正经”,但这种俏皮亲近的对话,也正是另一种真诚。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宫子)
【非正常花絮】
记者手记
2016年的时候,黄晓丹发现她周围有很多号称遭遇中年危机的朋友。装作青年,他们已经太老了,但作为中年人,又好像还太年轻。在他们把孩子哄上床,锅碗收拾好的夜晚,微信群里开始混杂着心理困惑和读书心得的对话。不久之后,在这些老青年们的要求之下,群里解释心理问题最多的咨询师庄磊和解释文学问题最多的黄晓丹就被迫开了一门结合古代文学和现代心理学的网络课程。
但没想到,这个课程的预告刚发出来,就跑来了一堆学生报名。她预感到,“这群孩子又要做傻事了”。于是,他们被挨个质问。有个每天都在中文系游荡的商学院男孩说,是因为特别喜欢听她的课,“可是我每周都在教学楼里讲10节课,也没看到你来旁听啊”;有个天天半夜被考研时间表吓醒的姑娘说听课是为了复习古代文学,然而黄晓丹打发她去背书了。最终,她成功地把学生们都挡在了课程之外。
她想好了那些课程不是讲给学生们听的。她说:“教师是一种演员”,她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展现的应该是一种经过理性过滤的自我形象,为学生带来符合其专业目标的思维训练和总体来说积极的情绪感受。她更喜欢与他们聊天,当一个倾听者。
黄晓丹非常喜欢听各种小朋友的故事。图中所说的“只会煮饭不会做菜差点被打”的男生,就是《书评周刊》的记者宫子(宫照华)。
第一次上她的课,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个成天自以为是地捧着一本《存在与虚无》坐在教室走神的“怪物”。第一堂课就对她产生好感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这个老师长得太好看了,这在大学里还是蛮重要的,尤其是上一堂课还会有某个口齿不清的中年人吹嘘自己去过朝鲜旅游、会用童子尿酿酒的情况下;第二点,她一上来就说自己期末绝对不会考课本和PPT上面的内容——这可太好了,就喜欢这种用不着记笔记的课。但是后来发现,一门课真正好听的时候,记笔记就变成了忍不住的事情。虽然写在课本上的都是些不完整的句子,非常随意,没有逻辑,但看到那些字词就能想起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天气。
不过我从来都不说话,也不提问题,一直坐在传说中最后一排靠窗的“贵宾座”上。所以一年过去了,老师也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好在她是一个非常愿意听小朋友讲故事的老师。那一年里,她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独特的课堂作业,每周都要写几百字左右的个人感想。每个人写的东西都不一样,有规规矩矩写自己对陶渊明、三曹、李白和杜甫的心得体会的,也有在作业里写那些年轻人常见的问题,诸如如何寻找自由,如何面对家乡的性别歧视等等,还有从第一次作业就抄百度百科一直抄到最后一次的。每份作业上都能看到她的反馈,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那些抄百度的作业上就写着她无奈的请求,从颇富哲理的“写作是为了找到自己真实的声音”一路降到“不要抄了”、“再抄你就不要考试了”。
这就是我们那一年里的交流,听起来更像是笔友。直到那个学期结束,她把班上所有同学的作业整理成了一个小册子,印刷出来,那个时候她才知道我是谁。和所有人一样,没见过我之前,她也以为我是个女生。她给我这个躲在人堆里走神的学生起了个外号,“壁虎同学”,并且写了一篇散文叫做《壁虎同学现身记》。
2014年,由古代文学课学生作业结集成册的《琅叶集》
那是我最后一学期认真地上课。更换了老师后,在接下来的学期里,我几乎再也没去听过古代文学课,把所有时间耗在了图书馆里乱逛,读小说,直到收到了同学转达的其他教授的警告——这个人如果再不来上课的话,就不要参加考试了。
对谈
(侥幸毕业两年后,兔老师与那个成天翘课的壁虎同学又一次相遇。大家都还是老样子:她还是穿着长裙和她那买了五双穿了七年的rockport的超轻鞋,壁虎同学还是每天读着不知道来自哪个国家的外国小说,自娱自乐地做着选题。在外面有不少蚊子的夏天咖啡馆里,《诗人十四个》里的场景重新让他们回到了江南大学的蠡湖、雪浪山和长广溪,想起了春天的课堂和古代诗人的文学课)
中国诗词中的主流与另类
宫子:搜肠刮肚后,发现我喜欢的古代诗人还是有几个,比如说,柳永,姜夔,秦观。有一阵子还喜欢李贺和李白来着。但看得很少,我一首完整的诗词也背不上来。像陶渊明和杜甫这一类的诗人,我倒是理性上知道他们写的很好,但就是没那么喜欢。这种选择倾向是不是有些奇怪?
黄晓丹:其实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的猜测是,欣赏陶渊明、杜甫、苏轼的诗,它其实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事情,它需要一种经过中国传统文化驯化的情感。我们很难靠天然的本性去喜欢它。比如说柳永那种“多情自古伤离别”或者秦观那种“有情芍药含春泪”,无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拉美人、一个巴尔干人还是阿拉伯人,都能够理解。那就是人情和自然之美的直接的触动。但陶渊明,以及我们中国文化中认为更“高雅”的那一类作者,比如苏轼、王维,什么是“种桑长江边,三年复当采”,什么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什么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都需要包括时代背景、哲学思想的讲解,而在这些讲解中,还有一层是建立在历史和哲学的背景之上,而光讲历史和哲学却仍旧不能抵达的,就是境界。那境界是什么呢?我觉得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一个诗人将他的人生际遇、人格力量和对历史哲学的思考转化成一种审美化表达的能力。
如果只有那些际遇、思考,但是转化不成美不行,但如果只有美的形式,却没有背后真实的支撑也不行。一个人是不可能天生能对江边一棵杂树、湖边一只傻鸟思接千古,并读取出背后各种历史文化的蕴含的,更不可能跳过历史文化的思维过程,直接产生某种准确、细微的情感的,不然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想象泛化和情绪泛滥的精神病性世界里了。
那么“驯化”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长期的后天养成,熟悉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中那些知性内容-审美内容-情感内容的既定链接,甚至可以跳过文本背后的知性内容,直接获得情感的触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诗话里写某人获某残句,反复讽咏,大为感动,而不知其本事为何,多年后知其本事,才确认当年的感觉没错。既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学直觉的训练,也可以说这是文化对人的驯化。
黄晓丹
宫子:看来是我太不中国了。
黄晓丹:没有没有。确实你被驯化得越多,你就越能理解那种情感,但我并不觉得没有经过这个驯化就是个多么不好的事。说个好玩的事,前不久我去言几又给一个朋友的新书发布会捧场,那个书店的经理非常想好好招待我们,他看我是个女生,就和我说“等下他们谈的那本书看起来很难的,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不如跟我去做香水吧”,于是我就去上了一节香水课。香水课的老师说了个很好玩的事。他说:“为什么大家都说薰衣草有助眠的功能,西方的助眠喷雾都是薰衣草味的?那是因为西方人习惯在洗衣过程中加入薰衣草,所以当他长大出门在外,焦虑难眠时,在枕头上喷点薰衣草香水,就好像回到了家里。中国人要是做睡眠喷雾,得用檀香皂或者六神吧”。我被他的智慧惊呆了,因为我出门的时候真的往包里塞了一小瓶檀香木精油。气味的驯化和文字的驯化没太大区别,甚至更顽固,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规定每个人都使用同一种气味入眠呢?
有些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在初中或者高中时代,在文化荒芜的环境里自己找到了一些获取知识的渠道。有的读了很多中国文学、有的读了很多日本文学,像你这样的是比较奇怪的,反正我对你读的那些作家只有一个印象,就是都住在和中国不通直航的地方。这样一种野蛮生长,带来的是对文学非常自主、广阔的接触,当然会带来欣赏眼光的不同。你今天在书评周刊做记者,终于把在课桌下面看闲书变成了职业,而且可以更随心所欲地挖掘世界边边角角的作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良性的自我驯化,我一点都不觉得想要把你掰回去学习唐诗。
宫子:有可能是这样。不过我还是挺喜欢柳永的,柳永那么潇洒的词人,在中国历史上真的太罕见了。
黄晓丹:非常少。我发现你喜欢的中国古代词人,都有种共性。要么像柳永和姜夔,没有做上什么官;要么像秦观,虽然做了官,却不在词里表达士大夫的感慨。和你谈话很有意思,因为你这样一说,我反观我喜欢的诗人,都更多地在作品里表达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文化教养和审美品位,尤其是审美品位,我喜欢陶渊明、王维、晏殊,可能都是这个原因。
中国诗歌史中有诸如“雅郑”“正变”这些话题,审美批评的主流也还是温柔敦厚。你喜欢的那些基本是非主流。在中国诗歌的审美方面我很传统,就是喜欢温柔敦厚、明丽修洁的,要我讲李贺、讲柳永我就很痛苦,这可能也是驯化的结果吧。
诗人陶渊明画像。
宫子:对,李贺我也喜欢。我不喜欢那种“香草美人”寄托家国情怀的传统,我觉得那非常单调。
黄晓丹:“士大夫”首先是一个阶层,然后是一种身份意识,再后是一种审美习惯。这个阶层首先在社会层面消失了,但身份意识会在阶层实体消失之后继续存在很久,我身边就有很多不是读古典文学但具有士大夫精神的人。我有一个公务员朋友,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因为他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写作他对于国际形势的观察、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上达天听,对社稷黎民有益。所以上次他来无锡体检,虽然下着暴雨,我还是把他带到了东林书院,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前照了相。你说的“家国情怀”、“香草美人”更多还是在身份意识层面,但我觉得会持续更久的是审美习惯。比如现在网上会流传雍正和乾隆审美品位对比的有趣文章,大部分中国人看了都会会心一笑,这就是这种审美品位的遗留。说不定你可以给你关心的那些住在各种奇怪地方的作家设计一套测试题,看看他们的审美是更接近乾隆还是雍正,他们对中国人能感受到的“雅”是何种感受?
宫子:可能我喜欢的都更加个人化一点。
黄晓丹:在现代以前的社会里,一个人不太可能以一个个体的方式生活。大部分作者以士大夫的身份生活,等到明代之后,书籍出版市场发达了,作者才可能以畅销书作家的身份写作,像冯梦龙之类的,但他们主要写的文体也变成了小说和随笔。你说的这点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做老师的罔顾学生自己身份认同,一定要摁着他们去为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感动,这也是挺费劲的。理想的状况是向学生介绍更多的古典文学作品和读法,让学生能找到和自己匹配的作品。
“传统文化热”与个人的阅读选择
宫子:但现在好多人觉得,不理解这些古典文学,不理解传统文化,就不是个真正的中国人。
黄晓丹:为什么人们有时候会怀疑自己不是中国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除了中文,并没有掌握一门其他语言,也没有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置有房产、拥有护照,如果你不是中国人,还能是哪国人?文学性的语言有时候听起来很有情感的冲击力,比如“不会背唐诗宋词,就不是中国人”“没见过黄河长江,就不是中国人”。但事实是,这个国家幅员如此辽阔,从墨脱到黑河,总有人没有见过黄河长江、不会背唐诗宋词,但他们仍然还是中国人。我们要警惕对于“中国”概念的狭隘化。当然从深里来说,从鸦片战争以来,在整个近代因为中国饱受冲击,自我认同受损,常常处于“自我神话”和“自我贬低”循环往复的分裂性认同中。这就像青年人总是一会儿觉得自己天纵英才,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块废柴。但随着个人和国家的成熟,更稳定的认同出现,“我到底是谁”的焦虑就会减轻。
李白,中国唐代大诗人。
宫子:可还是有很多极为“迷恋”传统文化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种每天穿着古装去上课,写古诗,连发个朋友圈都要用文言文的同学。
黄晓丹:有啊有啊。对我来说这是个很纠结的事啊。我是个爱美的人,所以我觉得穿汉服也好,穿旗袍也好,穿西服也好,都要穿得美才行。但在日常生活中汉服穿得美的人是极为少见的。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看香奈儿的传记就知道,现在服装工业是极简化的机器生产,找到了成本和审美之间的最佳比值,而汉服要美,从设计到面料到手工,花费远远高于时装,以购买现代时装的预算购买汉服,那肯定是不会好看的呀;二,服装需要和环境相匹配,现代城市其实已经改变了人们观看的方式。比如我们看现代建筑,看它的体量、造型、立面、光影关系,而不是看细节的雕梁画栋,而几乎所有国家的古代服饰之美,都是建立在绫罗绸缎的颜色搭配和细节的绣花上的。
在大体量、远距离观看的现代都市中,欣赏汉服之美需要调整观看方式,所以我还是更愿意在博物馆和舞台上看汉服;第三说个接地气点的,在现实中,我就没见过人穿汉服而不搞折衷,所以我见过穿着耐克鞋穿汉服的
(因为要走路)
、披散头发穿汉服的
(因为不会梳头)
、背着书包穿汉服的
(因为没有书僮)
。所以我掂量了一下,决定还是不要穿汉服了,虽然有人说我头大,穿汉服应该还是蛮好看的……
宫子:作为一个教古代文学的老师,你怎么看有些像我这样的学生不爱学这门课?我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还是少数?
黄晓丹:学还是要学的,不然考试考不出怎么拿毕业证书?但在考及格能毕业的基础上,要大家都吃饭也看杜甫这不现实。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可以看,我们不会质问人家为什么没看过《伊利亚特》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什么一定要质问人家为什么没看过某唐代诗人的作品?他不喜欢这个诗人,也许他喜欢那个诗人;他不喜欢文学,可能他喜欢语言学;他对所有中文系的课都不喜欢,可能他喜欢当程序员。这都不要紧,只要他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越是有求知欲的学生,就越不能均等地对待每一门课,因为这里有精力分配的问题。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某个学生自己有非常开阔的阅读视野,那就意味着想在另外一个领域吸引他的注意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有那么多好看的东西,我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听你讲。这可能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情况。但大部分的学生不是这样的。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文学课是他们的课程安排中比较有趣、比较与个人生活有关系的课程,不管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还是外国文学都是如此。相比公共课和语言类课程,我觉得文学类课程想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是比较容易的。
如何在现代讲解古典诗歌?
宫子:据你观察,学生最喜欢哪些古代诗人?
黄晓丹:当他们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时,最喜欢的诗人基本就是纳兰性德、李后主、李白、苏轼。在大学古代文学课的学习过程中,曹植、晏几道、黄仲则也会比较容易接受。
宫子: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黄晓丹:这些诗人基本都是青春诗人、激情诗人,从人生体验上来说与青年人接近,而且行文比较直白,阅读起来也没有太多障碍。当然苏轼是个例外,苏轼基本是人见人爱。学生比较难以理解陶渊明和王维,但我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在我最新教的这一届,是00后的学生了,他们可以非常快地接受王维。有时我在想,这难道是因为真的进入“低欲望时代”了吗?当然这还要观察。而且对诗歌的阅读品位也是会不断变化的。
《李商隐诗集疏注》(作者: 叶葱奇 疏注;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宫子:对,这我很有体会。阅读品位的变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契机。我中学时特别讨厌李商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写诗,搞得和艾略特似的,到处都是什么用典隐喻,什么“蓝田玉暖日生烟”。再加上讲台上的老师一个劲儿强调,李商隐的那首诗有多么好,这就更不信了。感觉那老师完全在胡说八道。但到了大学里,读了一本叶葱奇的《李商隐诗集疏注》,就体会到了李商隐真的是个很好的诗人。也有一些诗人,原来喜欢,后来就不喜欢了,比如张先。中学时可喜欢他的词了,后来感觉写得像QQ签名——“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黄晓丹: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古典诗词讲解者的身份定位问题。我们至少具有两种身份定位的可能:第一种将自己视为真理的宣讲者、传统的代理人,认为自己讲的东西都是对的。那这样就会不管在写作还是上课时,都带有一种宣示教义的意味,如果听众不爱听,那就是听众的审美品位的问题。这样的身份定位有两个问题,第一它不友好;第二,当讲授者自诩为圣人门徒时,也就失去了诚实袒露自我生命、自我困惑的机会。所以只有当讲授者愿意放弃一些权威性,他才能换取自我的现身。
宫子:那么这种自我现身是否意味着放弃客观性?我注意到这本《诗人十四个》出版后,也有声音认为其中有些解释过于个人化,比如你用荣格的炼金术心理学来解释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黄晓丹:首先,认为自己能把握绝对的客观性,这本身是一种自大。我们可以审查自我相对于另一个人的偏见,比如我可以自我反思,认为我读李商隐的《碧城》感慨万千,但我隔壁某老师并没有,可能《碧城》中投射了很多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们很难审查那些来自于更大背景的偏差,比如来自于文化背景的,更难审视来自于语言结构的偏差,因此对于一个讲解者来说,不管他采用自我彰显还是自我隐身的言说方式,都要知道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其次,相对的客观由什么保证呢?第一由阐释传统,就是不能完全抛开这首作品的阐释传统瞎说,但可以在介绍了阐释传统的继承上,再加生发。第二是由复调性的阐释生态,就是当读者可以阅读多种阐释时,那么任何一种阐释中的主观偏差就能被另一种阐释中的另一偏差所纠正,我们古代的集注集评就是这么干的。
杜甫。
宫子:其实我觉得主观因素的加入没什么不好。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内心世界一定是不同的。如果讲的东西都是一成不变的,那也就没有必要再讲了,看以前人讲的就足够了。
黄晓丹:是的。一个有意思的诗歌阐释者就是一个旅行家。他到了一个地方去旅行,回来后只是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一部分的见闻,而不是对那个地方的一种教科书式的全景介绍。正是因为他的见闻是片面的,带有他个人的倾向,个人的色彩,甚至是发生在他身上的偶然,所以这样的讲解才是鲜活的、带有人情味的。我把心理学作为工具介入到诗歌阐释中来,也是想回答心灵是如何以生活为原材料生产出诗歌的。但如果一个游记和百度词条一样,按照既定的套路,使用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言,依次写着“国情概述”、“历史沿革”、“自然环境”、“杰出人物”,那它肯定不好看。我们讲解诗歌也是这样,如果讲得和百度百科一样,也是按照一定的套路、按部就班,讲述一套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孤寒身世、爱国情怀,那么诗歌中某些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消失了。一个讲解者必须意识到,他讲的东西是片面的,但也正因为是片面的、个人的,所以才是不可替代的。
宫子:一定要在自己真正有所感触,有想要讲述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才有可能讲好。
黄晓丹:而且我觉得一个作者只意识到不是在为所有人写作,一个老师只有意识到不是在为所有的人讲课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创造。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要为所有人写作,要对所有人讲课,任何普通人都没有办法驾驭这么大的主题。所以他最后更可能变为一种流于平庸的复读。这个问题在文学写作上不难理解,恰恰是那些在生前没有什么读者的作者,他们会写得更好,会成为最伟大的作者。因为他写的时候,他所需要取悦的只有几个人,这几个人说不定还生活在未来或者某个遥远的山洞里,因此他反而在写作中获得了一种自由。但对于那些每写一个字就得考虑如何获得10万+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是不存在的。
这种规律迁移到古典文学的阐释性写作领域中,我觉得也一样。现在传统文化热,看似古典诗歌的阐释者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但他们真的比那些生活在只有少数人关注传统文化的时代里的阐释者更好吗?或者说,他们写得更快乐、更自由吗?
《秋空爽朗——童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作者: 艾伦·奇南;译者: 刘幼怡;版本: 东方出版社,1998年9月)
宫子:现代的古典诗歌阐释作品基本是两种,一种是特别娱乐化的,希望用几分钟就能让所有人都读懂唐诗,另一种就是特别学院化的,就是我就按我的规矩讲,你怎么想我不管。但不管你写哪种,都会有人不爱读。
黄晓丹:对啊,你说你怎么可能把一个诗讲得既要符合小学生的审美品位,又要符合老干部的审美品位,还要符合大学生的品味,还要符合你这种人的审美品位。做不到的。众口难调,这连肯德基都做不到。
宫子:那我们想远一点,如果你可以一直自由自在地写下去,你准备在文学阐释的路上走多远?对于文学阐释到底能解决一些什么问题,跨越哪些看似不能跨越的边界,你有没有一个范本?
黄晓丹:也许是艾伦·奇南的《秋空爽朗——童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或者是河合隼雄的《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那样的作品吧。
宫子:那真是在走神的路上走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你明天就要去旅行了,祝你旅途愉快,替我向卡夫卡那古怪吓人的雕像问好。
黄晓丹:好的,我还要去找一下荣格的塔楼。我已经查好路线了,从苏黎世火车站坐一个小火车,再在乡间走半小时就能到。如果他梦中的翠鸟是真实的,那我在这本书里所写的一切联想也就是真实的。
作者:宫照华(宫子)
编辑:走走 罗东
校对:薛京宁
评分完成:已经给 狂心中 加上 300 银元!